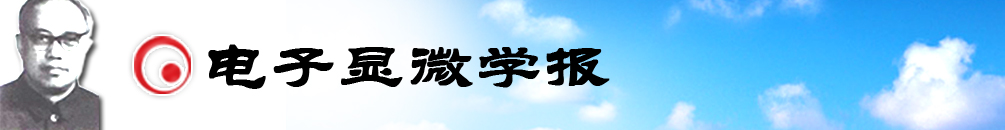四十年科研生涯的自我突围—— 我眼中的隋森芳老师
施一公
隋森芳是我的老师。他不仅仅是因为卓越的学术成就而被我尊称为老师,还因为他的的确确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教过当时还是本科生的我,讲授《生物物理》,是实实在在的任课老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清华生物系刚刚复系重建,百废待兴,方方面面都无法与拥有强大生物学基础的北大复旦武大相比。但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第一批留学生开始回国教书育人了,清华恰好是理想的回归之处。隋老师1970年在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算是“新工人”;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5年去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留学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大部分留学生学成之后选择继续留在海外长期工作生活,但是隋老师在1988年底毅然回到自己的母校,并开始承担教学、科研任务,至今已经整整37年。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隋老师讲课不多,但每节课都极其严谨、认真,观点犀利,常常在黑板上推演公式,对学生要求也比较高。
清华生物系的实验条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简单,既没有复杂先进的仪器设备,也严重缺乏研究经费。即便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隋老师选择研究课题的视野特别宽、跨度特别大。可以说,从德国博士毕业后回到清华的前面15至20年,隋老师运用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的各种研究手段,对一系列功能截然不同的蛋白质和复合物,都进行了深入探究。大约在2002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清华短期访学,隋老师和我深入交流了天花粉蛋白(Trichosanthin)对细胞内体形成和代谢的影响,我对他完全靠自己摸索进入细胞生物学的核心研究领域感到很诧异、也很感佩!
正是通过对天花粉蛋白这个课题的讨论,使得我认识了隋老师的博士生张帆。张帆博士毕业后到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她的科研素养和课题攻关能力都让我刮目相看。可以说,一般博士后无法解决的科研障碍在张帆手里都会被逐一化解。从张帆的科研能力上,我窥探到隋老师培养学生的独到之处!几乎同期的王宏伟和后来的白晓辰都是隋老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代表。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隋老师做出了一系列非常优秀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工作。
2009年,隋老师研究组运用冷冻电镜解析了一个细菌蛋白质量控制系统DegP的碗形寡聚化结构,在领域内倍受关注;2012-2015年,解析了NSF、SNAP-SNARE等多个与膜融合相关的蛋白和复合体结构;2005年,开始对藻胆体(Phycobilisome)的研究,在前期使用负染电镜研究的基础上,在2017年,解析了来自红藻的藻胆体冷冻电镜结构;2020年,对藻胆体内的电子传递机制做出基于结构的诠释。这些突破性成果,以及光合作用系统II的相关研究,使得隋老师课题组在光合作用机理研究领域在国际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隋老师有着独特的研究风格。他对研究有着深刻洞见,几十年如一日地追求重大的科学问题,既执着于同一个课题的持续研究,也常常大胆突入其它领域和新颖课题。跟隋老师讨论研究课题,能感受到他锐利的目光,不仅刨根究源于当下的数据分析,也时刻在探寻新的问题。他的课题范围非常宽,也鼓励学生尝试最重要最前沿的课题,不受任何拘束。甚至在2023年还出奇兵在核孔复合体(NPC)的结构研究中取得突破,解析了来自酵母的原子分辨率的内圈(Inner Ring)结构,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来自酵母的近原子分辨率的NPC结构。
1984年,清华大学生物系恢复重建,隋老师从刚刚复系的物理系调到生物系,成为第一批教师之一。从那时算起,隋老师从事生物学研究的科研生涯已经整整40年。这四十年,隋老师一直在突破条件和环境的限制,在科学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对重大科学问题的执着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我辈学习、也一直令我敬佩。
从隋老师1970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算起,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他不仅践行了清华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承诺,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在科学研究之路上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彰显了老一代科学家独特的求学、探索、引领这一曲折而辉煌的历程。